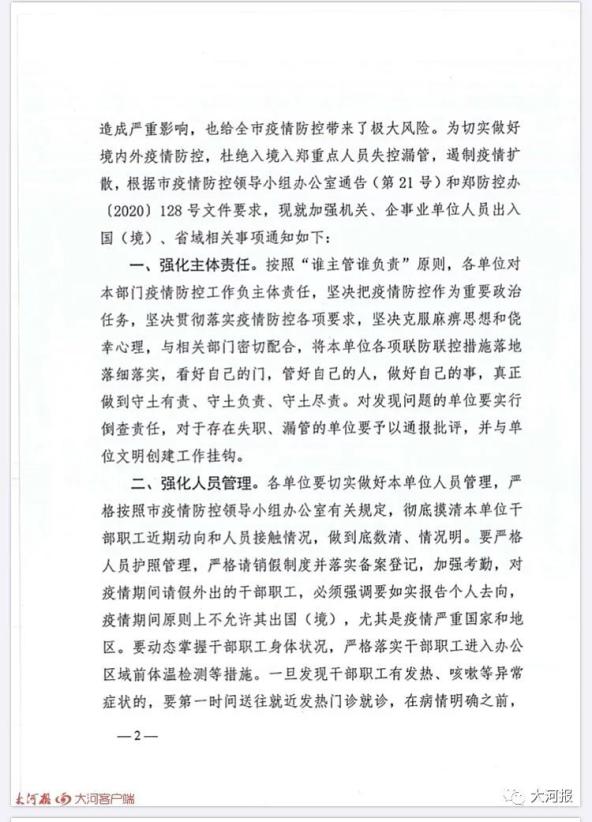站在南京东路与广西北路的交汇处,时间仿佛被压缩成了一本可以随意翻阅的画册,左手边,是南京东路——那条被誉为“中华商业第一街”的十里洋场,霓虹流火,人潮汹涌,国际品牌的巨幅广告在百年骑楼上闪烁,投射出一个全球化、消费主义的上海幻梦,右手边,是广西北路——一条不起眼的岔道,窄仄,幽深,像一道被遗忘的皱纹,悄然嵌入这片光鲜肌理的深处,我选择转身,拐进这条岔路,不过一步之遥,鼎沸的人声、炫目的光潮便骤然退去,如同按下了静音键,这里,藏着另一个上海,一个在宏大叙事背面,依然从容呼吸的日常上海。

广西北路,是一条用嗅觉开启的街道,甫一进入,南京东路上那混合着香水、甜品与空调冷气的标准化商业气息,瞬间被一股更生猛、更复杂的气味所取代,那是刚出锅的生煎馒头底部焦香混着肉馅的油润,是老大昌橱窗里奶油蛋糕甜腻的芬芳,是熟食店里挂着油光锃亮的烤鸭与酱色肋排的卤香,是午后老式发廊里飘出的廉价洗发水花香,更是从两侧斑驳弄堂口漫溢出的、家家户户正在烹煮的午饭气息,这气味,不精致,却诚实,它不试图讨好谁,只是忠实地记录着此地居民一日三餐的呼吸与代谢,是一种带着体温的、活色生香的“人间烟火”。
循着这烟火气前行,目光所及,是另一番视觉图谱,与南京东路那经过统一规划、尺度恢弘的欧陆风情建筑群不同,广西北路两侧是杂糅的、拼贴的,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、带有装饰艺术风格线条的公寓楼,与五六十年代的“新式里弄”比肩而立,再夹杂着八九十年代贴满白色马赛克的沿街商铺,建筑的立面,是岁月的留言板:褪色的油漆店招、锈蚀的空调外机、晾晒在竹竿上的万国衣物、从窗口探出头来的绿色盆栽……它们毫无章法地叠加在一起,构成了一种凌乱却蓬勃的生机,这种“乱”,不是破败,而是一种被生活反复打磨后形成的包浆,温润而富有细节。
这里的节奏,是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的从容,理发师傅在仅容转身的店铺里,为一个老主顾修剪着数十年不变的发型,慢工细活,聊着今年的黄梅天何时结束,杂货店的老板娘,一边守着摊子,一边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剥着毛豆,为晚饭做准备,几个老人围坐在弄堂口的树荫下,楚河汉界,杀得难分难解,身旁的收音机里咿咿呀呀地唱着沪剧,他们的生活,仿佛自有一套内生的、不受外界干扰的时间体系,南京东路上那些拖着行李箱、行色匆匆的游客,于他们而言,不过是窗外一道流动的、与己无关的风景,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主人,以一种近乎“大隐隐于市”的定力,守护着一种正在迅速消逝的、以邻里和熟人为基础的市井生活范式。
这份定力并非坚不可摧,抬眼望去,一些老房子的窗框已被卸下,黑洞洞的窗口像失神的眼睛,墙上用红色油漆画着巨大的“拆”字,触目惊心,推土机的轰鸣声,似乎已在耳畔隐隐作响,这让我想起不远处,那些被整体改造、焕然一新的“石库门”商业区,它们精致、整洁,却像被抽走了灵魂的标本,只剩下一个供人消费和拍照的怀旧外壳,我恐惧,眼前的广西北路,这片最后的“都市褶皱”,或许在不久的将来,也会被同样的逻辑熨平,变成另一段充满“腔调”与“风情”的商业步行街,入驻着同样的连锁咖啡与网红书店。
南京东路与广西北路,这两条相交的街道,仿佛构成了一个关于上海过去与未来的隐喻,前者是面向世界的、未来的、不断生长的上海;后者是面向内心的、过去的、努力存真的上海,我们当然需要那个光鲜亮丽、大步向前的上海,但若失去了广西北路这样能让人喘息、回望的“岔路”,这座城市是否会因失去记忆的锚点而变得轻浮?
我最终从广西北路的另一端走出,重新汇入南京东路汹涌的人潮,身后的那条岔路,像城市母体上一道即将愈合的疤痕,也像一本被翻到末页的、即将绝版的老书,我庆幸自己走了进去,用眼睛、鼻子和脚步,阅读了它最后的、鲜活的几页,这不仅仅是一次空间的穿行,更是一场与时间里那些柔软、坚韧部分的短暂重逢,在推土机尚未抵达之前,每一个这样的拐弯,都像一次抢救性的打捞,从遗忘的洪流中,为我们这个时代,打捞起一些关于“何以为家”的、温暖而确凿的证据。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