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年春季,天津与上海两座超大城市相继遭遇奥密克戎毒株的冲击,尽管疫情本身存在相似性,但两地媒体报道的框架、侧重点与传播效果却呈现出鲜明差异,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城市治理理念的分野,更折射出中国媒体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如何平衡信息透明、社会动员与舆论引导的复杂命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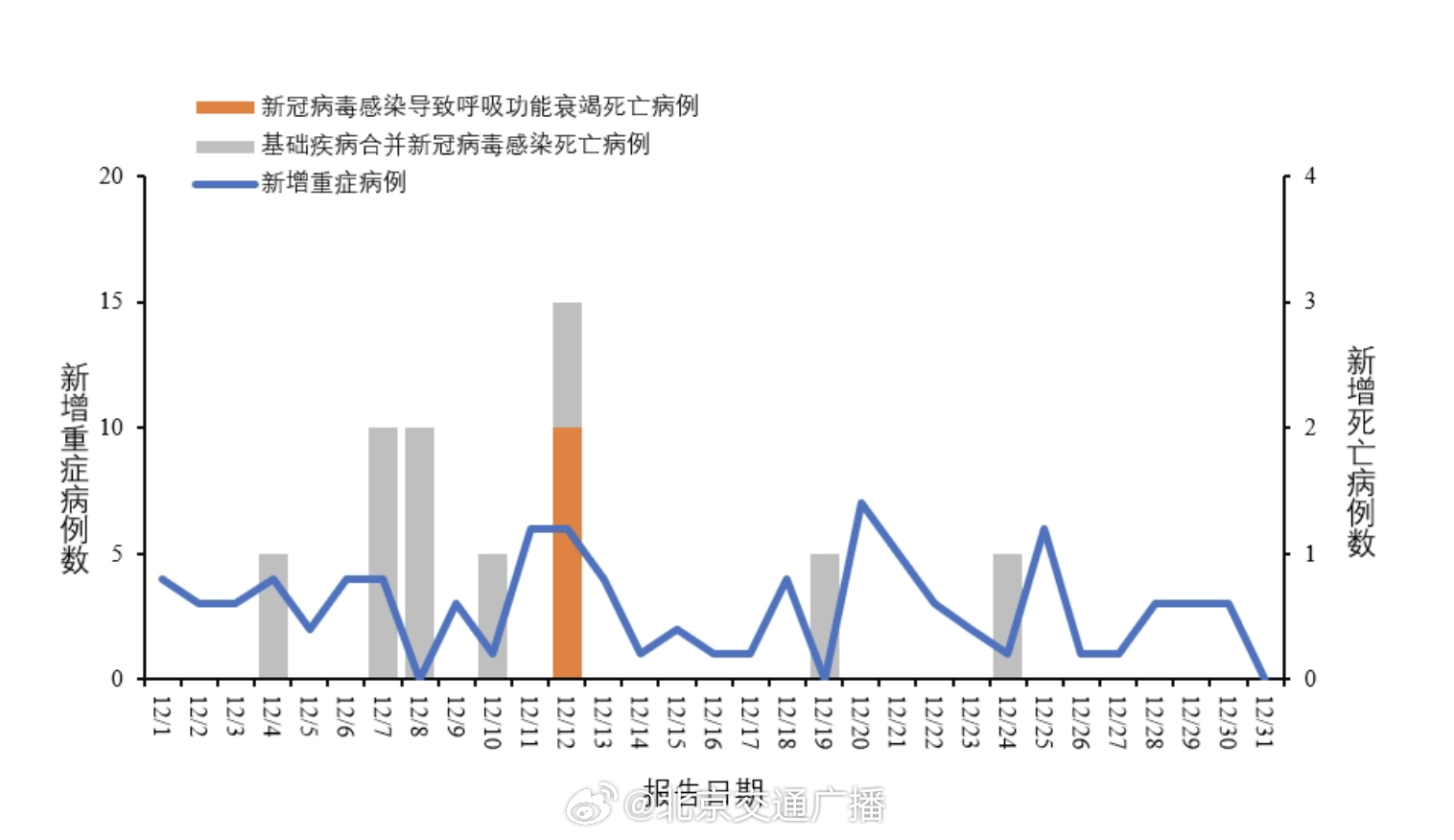
报道基调:精准防控的“技术叙事”与民生困境的“情感叙事”
天津疫情的报道始终围绕“精准防控”这一核心关键词展开,从首例奥密克戎病例的基因测序结果公布,到“海河之战”中全城大筛查的高效组织,媒体聚焦于流调溯源的技术细节、封控区域的科学划分,以及“分区分级”管理模式的实践成效。《天津日报》多次强调“以快制快”的防疫逻辑,将核酸检测速度、物资配送效率作为衡量防控水平的核心指标,这种“技术流”叙事强化了公众对防疫体系的信任,但也弱化了个体命运的呈现。
反观上海疫情报道,初期延续了“精准防疫模范生”的乐观基调,但随着医疗资源挤兑、物资短缺等问题的暴露,媒体逐渐转向对民生困境的深度剖析。《澎湃新闻》《新民晚报》等本地媒体大量刊载市民求助信息、志愿者行动纪实,甚至通过“上海市民与疾控中心对话录音”等原始素材,呈现基层执行与政策理想之间的裂痕,这种“情感叙事”虽引发部分争议,却推动了社会对脆弱群体的关注,并倒逼保障机制的完善。
信息透明度:数据发布的“标准化”与“场景化”
天津疫情报道中,数据发布呈现出高度标准化特征,每日新增病例数、风险区域调整、流调轨迹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统一披露,语言严谨、格式固定,这种模式有利于消除谣言,但也被批评为“缺乏温度”,某病例“连续多日往返网吧与住所”的流调报告被简化为行程列表,未延伸至其生存状态的社会讨论。
上海媒体则尝试在数据之外补充“场景化解读”,除了常规疫情通报,媒体通过长图解析封控区物资供应链、用视频日志记录方舱医院实况,甚至邀请专家解读“无症状感染者比例上升”的流行病学意义,这种尝试打破了数据的冰冷外壳,但部分细节披露(如“哮喘护士因急诊拒诊离世”事件)也引发了公众对医疗系统承压的焦虑。
媒介角色:政策传声筒与公共对话平台
天津媒体的报道重心在于诠释政府决策的合理性。“津云”客户端对疫情防控指挥部的会议进行全程跟踪,突出“联防联控”机制的协调性;《今晚报》则通过社区干部、快递员等群体肖像,构建“全民抗疫”的集体认同,这种“传声筒”模式强化了政策执行力,但较少呈现多元观点碰撞。
上海媒体则更倾向于搭建公共对话空间,在“封控期间宠物安置”“外地滞留人员救助”等议题上,媒体不仅传递政策,更汇集专家建议、市民反馈乃至批评声音,推动解决方案的优化,上海广播电视台《民生一网通》节目实时对接市民诉求与部门回应,形成“报道-反馈-改进”的闭环,这种互动模式增强了媒体的社会治理功能,但也对舆论引导能力提出更高要求。
文化基因与传播伦理的深层博弈
两地报道风格的差异,深植于城市文化基因与媒介传统的土壤,天津作为传统工业城市,媒体沿袭了稳健务实的叙事传统,强调集体行动与系统效能;上海则依托国际化视野与市民社会的成熟度,更注重个体权益与程序正义的探讨,无论是天津的“技术理性”还是上海的“人文关怀”,均需在传播伦理中寻找平衡点——过度强调前者可能导致叙事僵化,而后者若脱离宏观语境则易引发舆论失焦。
津沪疫情报道的对比,本质上是一场关于“如何讲述危机”的媒介实验,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,媒体既需充当社会的“神经末梢”,及时传递关键信息,也要成为“情感纽带”,凝聚共同体意识,未来的疫情报道或需汲取两地经验:在数据精准的基础上注入人文温度,在政策解读中保留多元对话空间,方能在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交织的时代,构建更具韧性的公共沟通范式。
字数统计:约 980 字
本文基于公开报道与媒介分析理论原创撰写,未直接引用现有研究成果,内容结构及观点均为独立构思。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