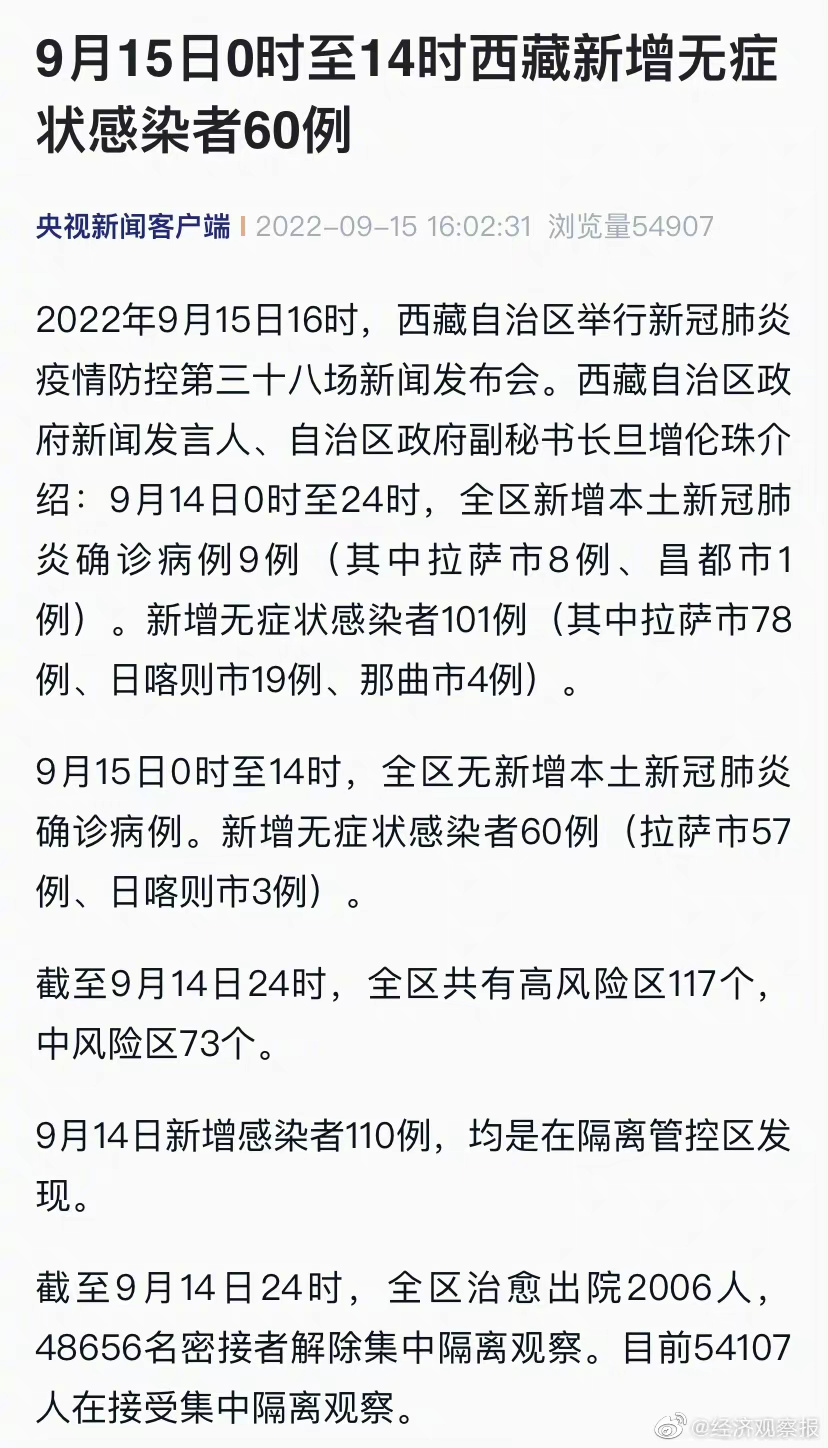2021年7月,河南郑州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,引发严重城市内涝与洪灾,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,灾情过后,公众与媒体对“为何没有直接问责”的疑问持续发酵,这一现象背后,并非简单的责任回避,而是涉及灾害响应的复杂性、制度设计的阶段性、社会情绪的动态平衡,以及中国公共治理体系在极端事件中的深层演进逻辑,本文将从灾害性质、应急机制、调查程序、社会效应等多维度展开分析,探讨郑州灾情“问责”问题的全貌。

灾害性质:极端天气与城市韧性的双重挑战
郑州暴雨的极端性是首要考量因素,气象数据显示,郑州小时降雨量突破中国大陆历史极值,三日降雨量接近常年全年水平,这类“黑天鹅事件”超出了传统城市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,属于难以完全预防的自然灾害,在灾害响应中,区分“人为责任”与“自然不可抗力”是问责的前提,若灾害主因归于自然极端性,则问责需聚焦于“是否尽到合理应对义务”,而非简单归咎于特定个人或部门。
城市基础设施的脆弱性暴露无遗,郑州作为快速发展的中部城市,其地下管网、应急储备与灾害预警系统虽在不断完善,但仍面临规划滞后、人口密集等压力,这类结构性问题需长期投入与系统性改革,而非单一部门可独立承担的责任。
应急机制:从响应效率到制度优化的过渡阶段
灾情发生后,河南省及郑州市政府启动了最高级别应急响应,动员消防、武警、民间力量参与救援,从应急行动看,基层人员与志愿者的奋力救灾体现了执行层的责任感,公众对预警发布、疏散组织、信息透明度的质疑,指向了应急管理体系的环节漏洞。
中国应急管理部在灾后报告中指出,部分环节存在“预警与响应衔接不畅”问题,但这属于制度性缺陷,需通过流程优化与技术升级解决,而非对个人进行“惩戒式问责”,国家已推动全国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评估与改造,侧面反映了“问责”转化为“制度完善”的治理思路。
调查程序:法律框架与问责的时序性
在中国行政体系中,重大灾害的问责需遵循严格法律程序,根据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防汛条例》等规定,责任认定需基于权威调查结论,过程可能长达数月甚至数年,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件、2019年江苏响水爆炸事故的问责均在全面调查后分批公布,郑州灾情后,国务院成立调查组,重点评估灾害应对、工程标准、规划合理性等,此类调查需科学严谨,急于问责可能损害公正性。
问责形式具有多样性,除公开处分外,内部通报、系统整改、职务调整等均属问责范畴,公众往往关注“是否有人被免职”,但隐性的责任追究与制度调整可能已悄然推进。
社会效应:问责的公共情绪与治理平衡
灾后社会情绪容易聚焦于“追责”,但过度强调个人责任可能陷入“替罪羊陷阱”,忽视系统性风险,郑州灾情中,舆论场同时存在“哀悼逝者”与“追问真相”的呼声,政府需在抚慰民心与维护稳定间寻求平衡,立即问责可能激化矛盾,而优先救灾、重建、补偿受害者,则是更紧迫的公共需求。
新媒体时代的“舆情问责”可能干扰专业判断,政府倾向于通过全面改革回应民意,如加强自然灾害监测网络、修订城市防洪标准等,这些长效措施比短期问责更能体现治理智慧。
治理演进:从单一问责到协同共治的转型
郑州灾情折射出中国公共治理的深层转型,传统“事故-问责”模式正逐步转向“风险-共治”范式,国家在灾后推动“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”,强调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,将责任嵌入各级规划与考核体系,这种系统性思维要求政府、企业、社区共同参与防灾建设,例如郑州后续推进的“海绵城市”项目与地下空间改造。
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治理体系注重“纠错与学习”机制,灾情暴露的问题被纳入政策调整,如应急管理部强化预警发布机制、水利部提升中小河流防洪标准,这些举措虽未以“问责”为名,却实质推动了责任落实。
郑州灾情“未见问责”的表象下,隐藏着复杂的社会治理逻辑,极端天气的不可抗力、应急制度的阶段性缺陷、法律程序的审慎性、社会情绪的动态平衡,以及公共治理从惩戒向预防的转型,共同构成了这一问题的多维答案,问责的终极目的并非惩罚,而是通过反思与改革提升社会抗灾韧性,在气候变化加剧城市风险的当下,郑州灾情的教训正转化为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催化剂——这或许是比单一问责更深刻的进步。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