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澳门到南昌,地图上不过一指距离,实际却是跨越千里的归途,当飞机的轮子触碰南昌昌北国际机场的跑道,一声轻微的震动将我从浅睡中唤醒,窗外,熟悉的红土地映入眼帘,那一刻,我知道——我回家了。
澳门的海风似乎还萦绕在发梢,咸湿的气息尚未散尽,而南昌干燥的秋风已然扑面而来,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空气在我的肺腑间交汇,仿佛一场无声的对话,在澳门,我是异乡人,说着拗口的粤语,适应着右舵车的方向;在南昌,我是归人,满口的赣语自然流淌,每条街道都刻在记忆深处。
澳门的味道是复杂的,清晨的茶餐厅里,奶茶的醇厚与猪扒包的香气交织;夜晚的葡国餐厅内,马介休的咸香与葡国鸡的浓郁缠绵,这些味道曾让我感到新奇,却也始终隔着一层纱,而南昌的味道是直接的,是瓦罐汤的滚烫鲜香,是拌粉的爽辣劲道,是藜蒿炒腊肉的独特香气,这些味道不需要解释,它们直接连通着我的胃与童年。
记得在澳门的第一个中秋节,我独自站在大三巴牌坊下,望着天上那轮与家乡无异的明月,手中是从超市买来的广式月饼,甜腻得让人想念母亲手作的芝麻糖,那一刻,我明白了什么叫“月是故乡明”,而如今,我终于可以在自家的阳台上,品尝着母亲特意留下的南昌月饼,酥皮层层剥落,芝麻馅香甜不腻,这才是属于我的中秋味道。
语言是另一重鲜明的对比,在澳门,我习惯了在普通话、粤语、英语之间切换,每种语言都带着特定的社交面具,而回到南昌,当耳边再次响起地道的南昌话,“恰饭了啵”、“作兴你”这些质朴的问候让我瞬间卸下所有防备,方言不仅是交流工具,更是身份认同的密码,它让我重新确认自己是谁,来自哪里。

两座城市的节奏也截然不同,澳门是不眠的,霓虹灯彻夜闪烁,赌场的喧嚣与市井的烟火奇妙共存,而南昌保持着华中城市特有的步调,清晨的八一公园里是老人们太极的身影,傍晚的赣江边是散步的一家老少,这种不紧不慢,曾让我觉得落后,如今却感到珍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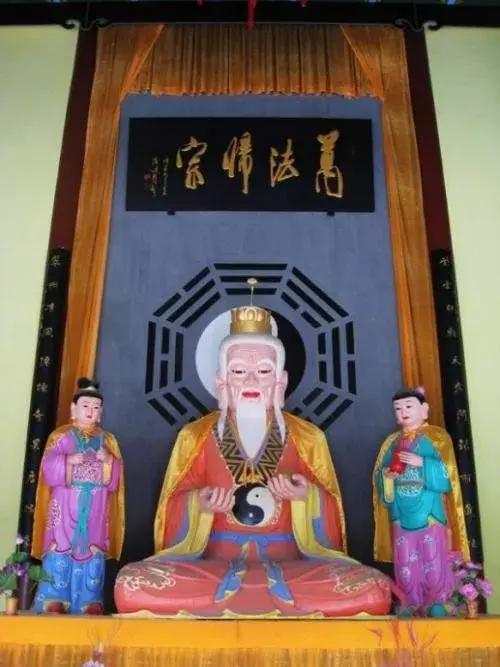
最让我感慨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态度,在澳门,每个人都在为生计奔波,高效率快节奏是生存法则,而在南昌,邻居会为了一锅好汤小火慢炖整个下午,朋友会为了一次聚会提前一周约定,这种对时间的“浪费”,恰恰是对生活最大的尊重。
从澳门回南昌,不仅是地理上的移动,更是心理上的回归,它让我明白,走过再多的地方,尝过再多的美食,心底最柔软处永远为家乡保留着一个位置,这座城市或许没有澳门的国际范,没有赌场的奢华,但它有我的根,有无法复制的记忆,有无论走多远都牵引着我的乡愁。
飞机完全停稳,我打开手机,第一条跳出来的信息是母亲发来的:“崽呀,汤炖好了,直接回家吃饭。”简单几个字,却让我眼眶湿润,提取行李时,我意外发现包里还有一个从澳门带来的蛋挞,已经冷透变形,我笑了笑,将它扔进垃圾桶——我要去品尝真正属于我的味道了。
澳门回南昌,这是一条味觉的归途,更是一场心灵的疗愈,在两个世界的切换中,我既拥有了澳门的开阔视野,也重新拥抱了南昌的深厚根基,这种双重体验让我更加完整,也更加清楚地知道:无论脚步走多远,只有回到这里,心才能真正安定。
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