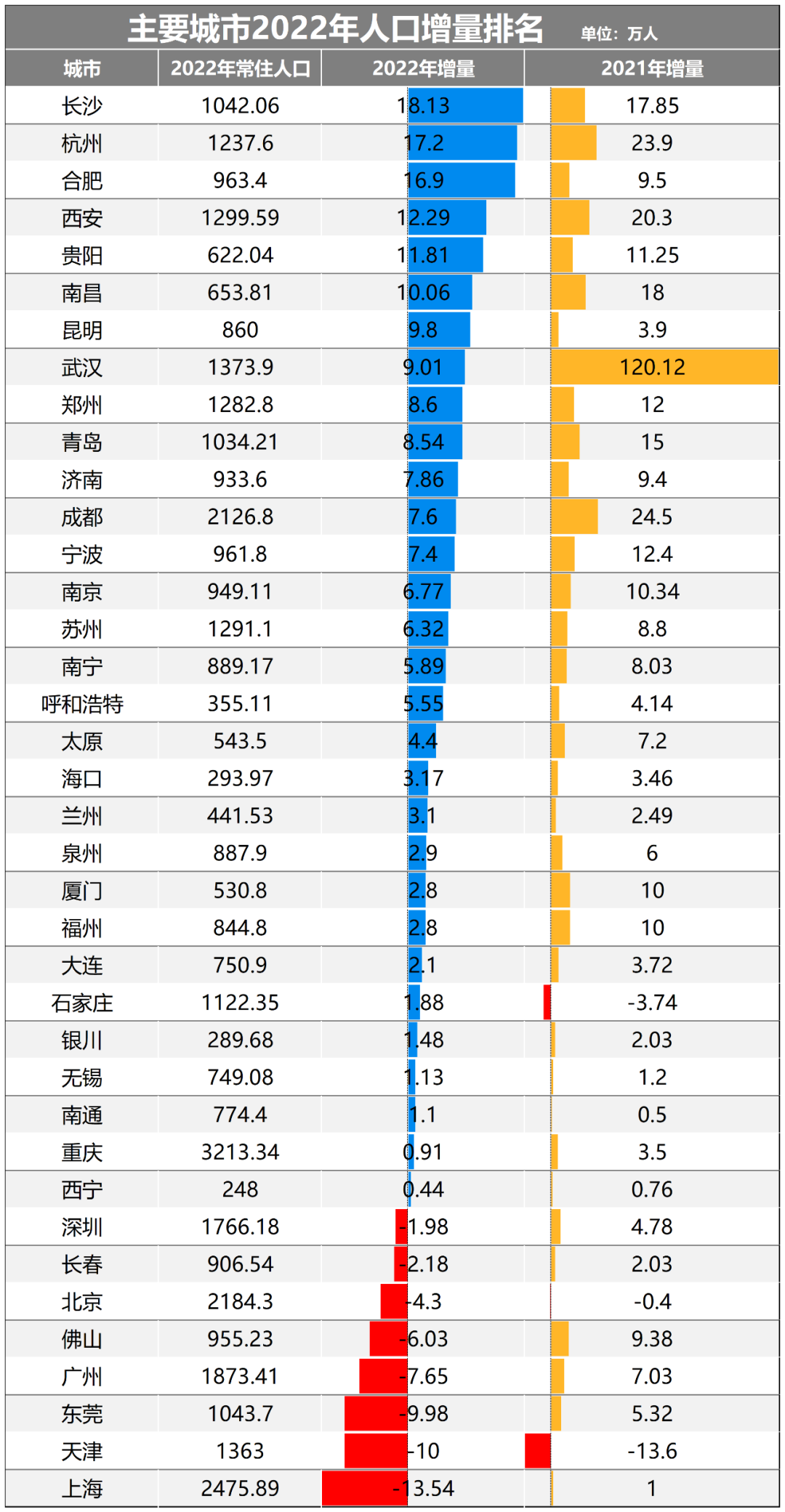当疫情的阴霾笼罩城市,不同地域的人们以其独特的文化性格,展现出迥然相异的应对姿态,在上海,可能是精细化的团购与自律;在武汉,是“不服周”的坚韧与悲壮;而在渤海之滨的天津,这场持续三年的“抗疫”之战,则被天津人演绎成了一场夹杂着快板声、相声梗和“嘛钱不钱的,乐呵乐呵得了”的豁达生活秀,天津人的疫情心态,绝非简单的乐观,而是一种深植于码头文化与市井烟火气的生存智慧,一种将沉重现实“解构”于幽默之中的独特心法。

以“哏”化剑:幽默是最高级的防护服
疫情初起,恐慌情绪蔓延,天津人的第一反应,往往不是抢购物资,而是“编段子”,核酸检测排长队,天津大爷能来一段:“间隔一米排好队,咱这不是买煎饼果子,别往前凑合!”小区封控,天津姐姐在群里发言:“好么,这回可真是‘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’了,咱也当回大家闺秀。”甚至连“奥密克戎”这个病毒名字,都能被天津人迅速本土化为“嘛克戎”,仿佛在叫一个不太招人待见的邻居。
这种无处不在的“哏都”精神,并非玩世不恭,相反,它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心理防御机制,将严峻的疫情、不便的生活,通过幽默和自嘲进行“降维打击”,极大地消解了其带来的心理压迫感,在天津人看来,天大的事,乐一乐,好像也就没那么吓人了,这种用笑声对抗不确定性的能力,让天津人在疫情的惊涛骇浪中,始终能保持一种难得的心理“浮力”。
“嘛钱不钱的”与“吃货”的执着:活在当下的务实哲学
天津人骨子里有股“恋家”和“知足常乐”的劲儿,那句经典的“嘛钱不钱的,乐呵乐呵得了”,在疫情期间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,当别的城市为股市波动、生意受损而焦虑时,很多天津人更关心的是:“介封控了,我哪买海货去?”“家里的面酱快见底了,这炸酱面要不香了!”
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极致专注,是一种务实的生存智慧,他们不执着于宏大的叙事,而是将精力聚焦于眼前的一餐一饭、身边的左邻右舍,封控期间,天津的社区微信群,往往是这样的画风:A家缺根葱,B家立马从阳台递过来;C家做了红烧肉,在群里晒图勾馋虫;D家孩子上网课需要打印资料,楼下的打印店老板想方设法“无接触”送达,这种基于“吃”和“人情”建立起来的互助网络,比任何空洞的口号都更具温暖和力量,它体现了天津人“活在当下”的哲学:既然无法改变大环境,那就先把自己的小日子过舒坦了,把身边的人照顾好了。
表面“躺平”与内里“绷劲儿”:分寸感极强的配合
外界或许会觉得天津人有些“吊儿郎当”,但真到了关键时刻,天津人心里那根弦,比谁都清楚,政府号召“非必要不外出”,天津人能把“听吆喝”执行到极致——真就搬个小马扎在楼下晒太阳,绝不跨出小区一步,要求全民核酸,无论是凌晨五点还是深夜十一点,队伍总能迅速排起,秩序井然,期间还夹杂着熟人之间的逗闷子:“您了也来啦?跟赶集似的。”
这种“表面顺从,内里自有章法”的配合,源于天津作为传统码头城市所积淀的契约精神和集体意识,他们明白,在大事上,个人必须服从集体,这是“规矩”,但他们又绝不会把这种配合搞得苦大仇深,总要在规则的缝隙里,给自己找点乐子,保持个体的舒展,这是一种极具分寸感的“绷劲儿”,该严肃时绝不掉链子,该放松时也绝不亏待自己。
曲艺魂与邻里情:流淌于血脉中的精神自留地
疫情期间,线下娱乐场所关闭,但天津人的文艺生活并未停滞,快板《抗疫英雄赞》在短视频平台爆火;一家老小在客厅里来段传统相声小段,录下来博君一乐;阳台音乐会上,响起的不只是流行歌曲,还有字正腔圆的京剧、评剧,这些深植于民间的曲艺形式,是天津人精神上的“自留地”,是抚慰焦虑、凝聚人心的文化密码。
被物理空间隔离的邻里关系,在疫情期间反而因祸得福,变得更加紧密,那种老天津卫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传统得以复苏,谁家菜买多了,分一分;谁家老人不会用手机,年轻人帮一把,在这种充满烟火气的互助中,个体不再孤独,共同构筑起一道温暖的心理防线。
回望疫情这段特殊岁月,天津人用他们特有的“哏都”豁达,完成了一次集体心理的“软着陆”,他们不是没有压力,不是没有担忧,而是选择用一种更高级、更本土化的方式与之和解,这种心态的核心,是将生活本身置于一切之上,用幽默化解沉重,用务实对抗虚无,用人情温暖冰冷,正如一位天津大哥所言:“病毒嘛玩意儿,它再厉害,不也得吃饭睡觉?咱该吃吃,该喝喝,嘛事别往心里搁。”这份源于市井、成于豁达的“天津心法”,或许正是我们在后疫情时代,最值得借鉴的一种生活态度。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